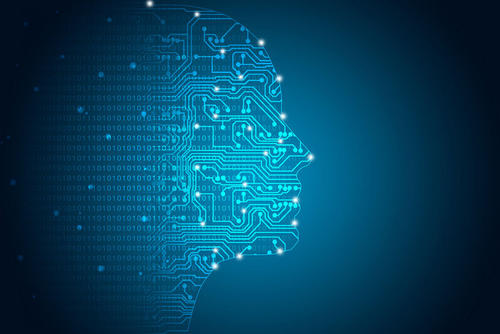阿萨姆的犀牛栖息地被侵犯者赶上了

在2018年5月的一个阴沉的下午,保护生物学家Bibhab Talukdar正在访问Assam的Pobitora国家公园。当他骑在公园核心的大象进入草原时,他遇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一个低矮的浓密草本植物的茂密生长,小绿叶和奶油白花。本植物,占卜冬洛尼奥斯科勒斯本地被称为“国会草”是美洲的本土和印度的外星物种。
Talukdar是国际公然保护联盟的主席(IUCN)亚洲犀牛专家组和Ngo Aaranyak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很担心,因为普宁市是一个高度侵入性的植物,具有历史损害20多个国家的当地生态系统历史世界。澳大利亚是伟大的榜样,大量牧场和夏季作物从杂草的压力下。
如果没有及时检查Pobitora的蔓延,Talukdar表示他认为,占度占地102个较大的一角犀牛(Rhinoceros Unicornis)拼写困难,通过窒息他们饲养的天然物种。
占度高占占地地区在施珀拉国家公园内的草原地区生长。保护主义者担心侵入性杂草将挤出本土饲料植物。照片由Bibhab Talukdar提供。尚不清楚额外的单度抵达印度。流行的理论是,种子抵达20世纪50年代,搭载了作为美国政府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进口的谷物的寄售。杂草首次报道1956年在浦那的垃圾堆中,在马哈拉施特拉国。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在Assam发现占度股,但之前尚未在Pobitora的核心领域报告。九年前,当Talukdar访问了公园,作为研究人员团队的一部分,研究了犀牛栖息地的侵入性植物的现状和分配,因此未观察到这样的寄生钠生长。“抵达公园似乎是最近的,”他说。
沉默的史德尔
普罗尼亚山是横跨阿萨姆的半十几种侵入性植物的最新补充,其中哈利斯在四个受保护区内超过三分之二的一角犀牛人群。
根据2011年杂志中的2011年文章,在Assam的犀牛范围内已建立的侵入性植物是Mimosa Invisa,Mimosa Micrantha(“英里 - 一个分钟”藤蔓),Chromolaena Odorata(Siam Weed)和Ipomoea Carnea(粉红色的早晨荣耀)。所有在2014年印度第五次国家生物多样性报告中被确定为负责损害当地生态系统的侵袭植物物种。
在玛纳斯国家公园的染色体感染区域。Chromolaena正在替代公园的本地植被。照片由Bikash Kumar Bhattacharya。“你必须加入占卜研处,艾奇拉赛车[水上架子]和Lantana Camara到该名单,”阿萨姆·农业大学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伊斯兰教学教授伊斯兰教教授伊萨姆·乔德哈特区。
Barua一直在几十年前研究博物馆的植物动态,他说,Assam的所有四个犀牛储备 -Kaziranga,Orang,Pobitora和Manas的国家公园 - 目前正在侵犯这些侵入性植物的攻击。
Barua说,每个都具有独特的危险。暹罗杂草和水葫芦是“司机物种”,能够在没有伴随环境变化的任何帮助下消除本土工厂;占嘌呤和含羞草具有极大的竞争能力,称为同一化合物,这抑制了这些杂草殖民地的土着植物的生长; Ipomoea茎形成厚厚的垫子,阻挡自然水流,使其在水封装后最麻醉的水生杂草,这对于堵塞水体是臭名昭着的; Lantana从根源中散发出毒药,杀死原生植物; Mikania每年生产大约40,000个种子,并通过窒息和窒息的草树苗,以非常快速的速度冒充森林地区。
“包括犀牛最受欢迎的饲料物种,包括犀牛的饲料物种,这是从这些入侵的直接压力下,”巴鲁纳说。
印度Muntjac也称为吠鹿,在奥兰国家公园内的一个地区看到了染色体,在那里,染色体已经开始感染。照片由Bikash Kumar Bhattacharya。不同的公园,不同的问题
在Kaziranga国家公园,每2018年人口普查2,413犀牛,含羞草在几个范围内可以看到超越天然草原。然而,自2000年代初以来,情况有所提高,当问题更为急剧。巴鲁斯近年来抵达了击中公园的自然洪水。
“在年度洪水期间,整个公园仍然是洪水,有时候几周。他说,这有点像对含羞草的生长一样的自然检查。“
然而,在公园的门口潜在的威胁是Ludwigia Peruviana(秘鲁水报数)。Barua领导的2017年研究发现,该半水生杂草已经损坏了在Karbi Anglong District的沼泽植物社区大约200平方公里处,位于Kaziranga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采取措施来检查其蔓延,他说Ludwigia可能会禁止Kaziranga Marshlands。
“Kaziranga国家公园非常靠近Ludwigia-Infested地区。因此,它可以是杂草潜入公园的沼泽地时的时间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加强守夜,那就可以在kaziranga内部在几年内到处。“
猩猩植物在奥兰国家公园。该植物被认为是帕特湿湿的草原下降的负责。照片由Bikash Kumar Bhattacharya。在Orang National Park,101 rhinos的家庭,Mimosa似乎是对生态系统最严重的当前威胁。从1987年到2008年,奥兰看到其湿的冲积草原缩小了12.8%,干燥的大草原草原和降级的草地分别增加了9.25%和6.51%,这主要是由于2011年的土地覆盖变化研究的影响公园。
玛纳斯国家公园也经历了一种植物,用染色体和米卡尼亚侵染了大量的森林。根据2004年调查,每平方米的密度为9.4至15.1株植物,Chromolaena正在超越沿着公园南部的植被已经过度植被的地区,而Mikania正在殖民地河滨草原补丁和森林边缘。
在Pobitora国家公园,最大的威胁是IPOMOEA,主要是草原的殖民地。公园内的IPOMOEA的传播引发了土着草地和杂草的竞争,适用于空间和营养。此外,随着Talukdar观察到的,占度占挑战。在去年,杂草已经被沿着公园的草原地区令人惊慌地蔓延。
Mikania植物在orang国家公园。Mikania也被确定为尼泊尔楚天湾国家公园的威胁,是世界上第二大一角犀牛人口的家园。照片由Bikash Kumar Bhattacharya。对rhinos的影响
犀牛已经遭受痛苦,因为阿萨姆的生态系统被这些侵入性植物击中。“首先,他们窒息和扼杀犀牛饲料的原生植物,导致饲料在保护区中饲料,”Talukdar说。“第二种,当紫罗兰这样的含羞草服用草原时,犀牛仍然难以放牧,这将使动物推向公园的安全性,从而使他们容易受到挖掘。”
认识到这些威胁,2019年2月28日由五个亚洲犀牛系列国家签署的亚洲犀牛宣言,已授权研究危及犀牛储备以及其他栖息地参数的侵入物种。
印度野生动物研究所(WII)的2015年报告持有侵入性植物,负责犀牛犀牛杀菌事件的增加。该报告称,包括Ipomoea的侵入性植物的快速增长以及公园内天然饲料物种的枯竭导致rhinos在园区的村庄中的作物袭击事件增加。
“因为侵袭性杂草正在窒息草原,犀牛越来越多地散发出邻近农田的作物饲养,”Pobitora的森林范围官员Mukul Tamuly说。
此外,一些侵入性植物含有有毒化合物,可以伤害rhinos和其他食草的摄取它们。“例如,Lantana Camara含有五环萜类化合物,一种称为Lantadene的肝毒性化合物。如果犀牛饲喂兰那的叶子,它可能会对他们造成显着的肝脏伤害,“Tamuly说。
西孟加拉达州墨坯国家公园的一个更大的一角犀牛。在该州的犀牛储备中也发现了包括Mikania的侵入物种。照片由Udayan dasgupta。战斗侵袭性杂草
成为成功入侵者的植物在快速增长,适应新环境。当他们被运输到生态系统,在他们的天然捕食者不存在的情况下,这些物种可以迅速超越土着植物。
“例如,占舱室的情况,”D.J.说拉贾克瓦,印度农业研究室(ICAR),长兰兰中心的高级农艺师和联合主任。“在印度之类的外籍环境中,它是自然的敌人,如墨西哥甲虫,Zygogramma Bicolata,只能在占度山叶上喂食。它给出了杂草的竞争优势和更多资源,以增长,繁殖,传播和最终超越土着植物物种。“
由于其更高的表型可塑性 - 在不同环境中不同的能力 - 侵入性植物可以适应环境波动。这有助于他们在新领域传播并建立。Rajkhowa引用了Mikania的示例,现在看到了一系列栖息地从陆地到沿岸的栖息地。
此外,许多侵入性植物本质上是神秘的,并且有多年来未经检测的能力,或者他们的损伤影响不会立即清楚,使得难以控制这些物种。
在奥兰国家公园中的森林补丁如此,特别容易发生植物植物。照片由Bikash Kumar Bhattacharya。鉴于这些挑战,有三种控制侵入性植物的方法:机械去除;喷涂化学品;并使用生物对照剂。
涉及手中的机械去除方法是最简单的方式,而是劳动密集型,昂贵,并且必须始终如一地重复。它广泛用于阿萨姆的犀牛储备,但产生了很少的结果。
“我们经常连制含羞草植物,但它们以非常快速的速度再次萌芽,”奥兰国家公园的森林范围官Chakrapani Rai说。“我们还应用了受控燃烧。即使是越来越徒劳无功。杂草的传播似乎是不可阻挡的。“
喷涂化学品被认为是不可行的保护区,因为它可能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影响。
生物控制方法,这是一种更复杂的过程,即需要释放在目标物种上饲喂的生物,被吹捧为一种较小危险和潜在有效的方法。印度的生物控制项目董事会(PDBC)是一家位于孟加拉堡市的政府机构的政府机构,负责确保无危害介绍,处理和释放生物控制剂的责任。
试图利用对阳律的生物控制已经取得了混合结果,在印度:植物的生物控制剂,墨西哥甲虫,在孟加拉鲁的成功结果表明,德里失败了。
Rajkhowa表示,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制定结合所有可用方法的计划。“在制定综合杂草管理计划时,生物控制应该是关键组成部分。在发现合适的生物控制剂,强调应该是机械去除。“
到目前为止,生物控制剂还没有用于ASSAM。但rajkhowa说他认为这是一种应该考虑的策略。“鉴于国家的温和性条件,它可能只是工作。”
奥兰国家公园位于北阿萨姆姆,是101犀牛的家。照片由Bikash Kumar Bhattacharya。但生物控制方法具有自己的风险:作为含有特定入侵者的生物防治引入的生物体也可能减少其他物种,进入入侵者本身。澳大利亚的甘蔗蟾蜍灾难的最昭着的生物控制般的例子。1935年甘蔗蟾蜍于1935年介绍,以控制昆士兰甘蔗作物的甘蔗甲虫。但在几十年的跨度,他们遍布澳大利亚各地,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害。
阿萨姆农业大学巴鲁说,他有利于探索其他替代方案。虽然他也赞同综合杂草管理计划的想法,但他表示,此类努力应优先考虑使用侵入性植物作为当地行业原材料的探索方式。
这方面有一些成功。水葫芦已被用来制作垫子和袋等产品数组;该工艺现在在印度东北部门雇用了大约3,500名当地工匠。Karbi Anglong中的蚕宝宝已开始使用Mikania作为Eri Silk的宿主植物,渴望主宿主植物,蓖麻(Ricinus Communis)。
研究表明还有潜在的商业利用Mikania到此目的,这可能反过来有助于控制杂草。距离玛纳斯国家公园附近的Bodo部落编织师正在使用Chromolaena作为天然染料,而Lantana被用作家具的原料 - 这是一项在控制杂草中取得成功的倡议。
“如果这些举措找到商业基础,”Barua表示,“他们不仅有助于有效的杂草管理,而且促进当地生计。”
(这个故事是第一次在Mongabay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