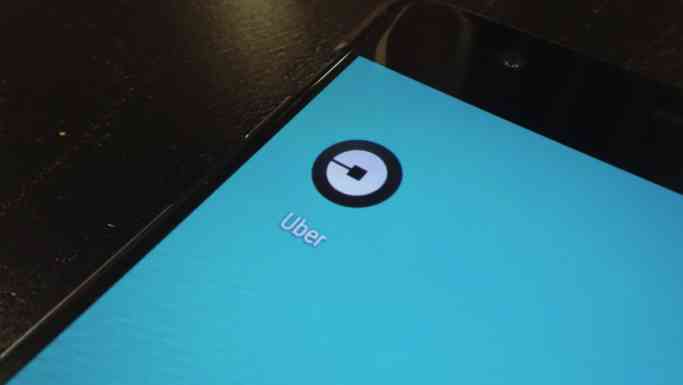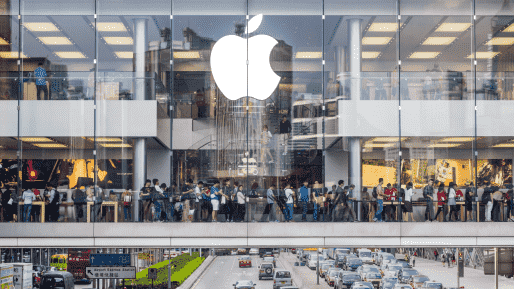【北国风光】哦,伊席次仁啊(上)
原标题:【北国风光】哦,伊席次仁啊(上)
致读者
今天,《内蒙古日报(汉文版)》改版后的首期《北国风光》周刊跟大家见面了。《北国风光》是内蒙古日报的老品牌,为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为自治区文化强区建设服务,《北国风光》《北国风光·文艺评论》《北国风光·文化》《北国风光·彩虹》4个版块,共同组成了《北国风光》家族。
文艺,肩负着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塑造中国形象的使命;文艺可以让人在喧嚣中找一片宁静,在疾速高压的现实生活中寻一处桃花源,可以让人理性地“看见”,还可以让人产生对“美”的顿悟、对“人”的悲悯……
《北国风光》在文学这块土地上已经坚守了几十年。几年前,80多岁的翻译家、编审那顺德力格尔先生满怀期待地说,希望在《北国风光》看到有充满牛奶味道的翻译作品。改版后的《北国风光》将推出翻译专栏“译草原”,让牛奶的味道飘起来。
《文艺评论》创办两年来,让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尚的作品照亮人心、温暖社会,一直是本版的追求。改版后的《北国风光·文艺评论》在保留原有栏目的基础上,新增了《谈艺录》《文艺家》《快评》《交锋》等栏目。
《北国风光·文化》将立足于我区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这一基础,为“弘扬草原文化,传承民族文化,挖掘内蒙古文化深厚内涵”而努力。
《北国风光·彩虹》,将通过《文艺地图》《独家发布》《疯狂秀》《艺苑快报》《公益进行时》《书画品鉴》等栏目,把多姿多彩的区内外文艺活动、综艺资讯呈现给读者朋友。
突出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突出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把先进的文化理念、文化精神、文化价值体现出来——改版后的《北国风光》周刊将继续遵循这一宗旨,为我区文艺事业的发展、草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贡献力量。 对《北国风光》家族而言,这次改版,有继承,也有创新;有摸索,也有坚持。6月,属于孩子,孩子,代表着爱与未来。《北国风光》周刊如同新生的婴儿,一定会在爱她的作者和读者的呵护中,健康成长。
□力格登 作品 哈达奇·刚 译
……从那时起,又过去了二十二年。
那时候,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句话,是个小有名气的人,是一群好哭、好流鼻涕、嘴馋、脸脏、豁牙子、光腚小孩队伍的领头,掏树上的鹊巢,逮滩里的跳鼠,追芨芨丛中的小兔崽,是个名扬二三十里远的“鼻涕大王”。要知道,争得这“大王”的称号还真费了些周折呢。一次,我们在河边的芨芨滩放牧牛犊,看见有个圆鼓鼓的东西,上前一看是个刺猬。这时,不知哪一个,在我后头挑逗,说:
“你常说自己是英雄,敢不敢踢它一脚?”
我一听,来了愣劲儿,提起脚丫就是一脚。当时,甭提有多疼了,可我怕丢面子,装作没事一样,用干土敷一下继续走。谁知没走几步又碰到一条黑花蛇。这时,又有人说了:
“你是英雄就抓住它。那我们就称你大王,跪在你脚下。”
“大王”的诱惑力太大了。我又充了一次好汉,拿棍子捺着蛇头,捏住尾巴提溜起来。这一下,我当定了英雄,得意洋洋地让他们跪下磕头,不料那蛇弯过脑袋差一点咬了我的胳膊。幸亏我扔得及时……不管怎样,他们从此叫我“鼻涕大王”,我也开始了“英雄”生涯,指挥“娃娃军”占领山头,占领蒙古包,占领喇嘛庙。有时盘腿坐在大佛像头上,让我的崇拜者们趴着磕头。
在我十二岁那年,像是从天上降下来一样,北浩特里来了个卷发小男孩儿。他穿一件斜襟褐袍,短袖筒掖在腰带里。我们娃娃军一下子包围住他,好奇地看着这位突然出现的陌生孩子。他那一双清澈见底的黑溜溜眼睛,怯生生地瞅着我们。说真的,他很漂亮。只在左耳朵上部有个筷尖大的小孔,可说是他身上唯一的缺陷。
娃娃军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但他像是一只让人逮住的野兔,眨巴双眼,不肯回答。大家的注意力终于集中到他耳朵上的小孔,便凭各自的小聪明做着各种猜测。
“这是为了戴耳环钻的。”“光腚”全帕拉说。
“不对,戴耳环不在耳朵的上部。”南浩特的“双鼻子”反驳。
“就在上部。”全帕拉并不服气。
“哈!将来,光腚全帕拉的媳归要在耳朵的上部戴耳环哪!”
“哈,哈!光腚全帕拉是个大傻瓜。”
“羞!羞!”
……
听阿兀(父亲)说,这小男孩是贡钦姨夫的侄子,叫伊席次仁,刚从老家来。贡钦姨夫从唐古特(青海藏族地区)来草原已经三十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唐古特人。
我们都喜欢伊席次仁,经常跟他一起玩。我们教他玩羊拐骨,教他骑牛犊,领他到野外辨认蒙古葱和野韭菜。连最好玩的地方——耳子崖下的石桌都让他去看过了。我还教给他用我的大黄狗捕兔子。可他不会带狗,甭说捕兔子,连个跳鼠都捕不了,还骂我的大黄狗是个饭桶。对此,我有点不高兴,因为他是刚来的,也就没怎么计较。
大约过了一年,他能凑合着讲好多蒙古话了。他有一副绳索式投石器。他投石又准又狠,棒极了。一次,他站在耳子崖下的石桌旁瞅准山腰上的一只豆鼠,只听嗖的一声,石头飞走了。等我们跑过去时,豆鼠的脑袋早已稀巴烂。我们个个佩服得直叫,伸出大拇指称他是神投手。记得从那次起,我们都试着制作长短不一、各式各样的投石器,但没有一个能用,只有伊席次仁的才能投石。我们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好。在野外放牧牛犊,谁都愿意搂着他的脖子走路,而我常常是头一个。
伊席次仁已经在我们草原住习惯,要上学了。
开学前——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八月份,我三叔从部队探亲回家。他是个军官,绿军装,大盖帽,威风极了。不过,他是我叔叔,我才不怕他哩!可伊席次仁就不同了,不知是怕他的一身绿军装呢还是怕他屁股上的匣子枪,惊恐地站在远处,不敢靠近。我三叔掏出几颗空弹壳让他拿去玩,他说什么也不要。我三叔打手枪可神了,所以年轻轻的就当了军官。一天,他并列摆好十个空酒瓶,说声“这都是敌人”便从左至右一枪打掉一个。到第十个小酒瓶时说那是“敌人小崽子”又一枪打碎了。我们高兴得拍巴掌跳起来。但伊席次仁不知怎么了,好像子弹是打在他身上似的,手捂着左耳朵,两眼像受伤的小兔似的,怯生生地滴溜溜转。大家不以为然,笑他是个胆小鬼,哈哈起哄。但是,我心里总不是个滋味,萦绕在我心头的他那怯生生的目光,就像前年见过的那只黄羊羔的目光一样。
前年冬天,我到三叔的部队去过年。那时,三叔刚从很远的地方完成战斗任务回来,趁着还没有下大雪,天天出去为部队猎黄羊。一天夜里,好说歹说跟叔叔去了。我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好奇地看车灯照射下挤在一起不敢走动的黄羊,被头顶上震耳欲聋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时,我看到几只没有中弹的黄羊不知往哪逃命,慌里慌张就地打转。其中有一只晕头转向的小黄羊羔愣愣地朝车灯跑来。我清楚地看到了它那雪白的前胸、小巧的嘴唇和四寸长的小嫩角。呵!多可爱的小家伙,好看极了,还带点傻劲儿,光知道往亮处去,不知道往暗处躲,瞪着一双可怜巴巴的眼睛,好像在向我求救。我心里怪疼的,最怕三叔开枪打死它。“别打死它,让我捉住带回家去养吧!”我敲着驾驶室棚顶对三叔说。
“捉不住,就算捉住了,没等你养活,你的大黄狗就会吃掉它的。”叔叔说。
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儿,小黄羊好像受了伤,很厉害地哆嗦了一下跑出了光圈。火扫帚般的灯柱再也没有照到它……
我觉得伊席次仁的眼睛,就像那只小黄羊羔的眼睛一样怯生生的,在向谁求救似的,我很可怜他。我制止住哈哈取笑的一群孩子,把他领到家里。不知怎么,我一看他的眼睛,总想起那只黄羊羔。后来,我干脆把他叫做“黄羊羔”。 我和黄羊羔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愿意跟我玩,也愿意靠近我,我对他也很好。到后来,我俩连睡觉都在一起了。我们合盖一床山羊皮被。有时,他把腿放到我胸口上,闹得我整夜做噩梦。有一次,我先起床外出时错穿了他的裤子,还闹了个笑话。
《内蒙古日报》2016年6月3日09版